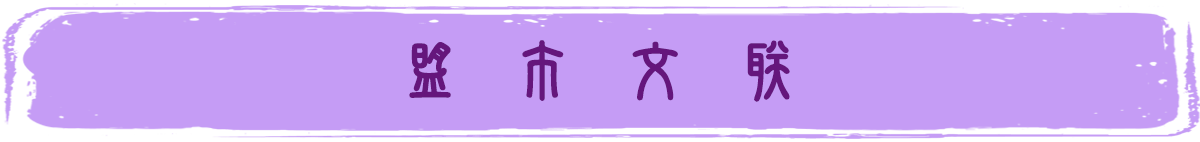
来源:乌海市文联 2022-12-15 21:50:17 阅读量:
近日
中国2022生态文学榜单公布
乌海作者刘惠春作品
《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入选
↓↓↓


/刘惠春
一
傍晚时分的黄河令人忧伤。
远处的太阳跌进了空空荡荡的荒原,乌兰布和沙漠变成一道起伏的青黑的线。河岸边的芦苇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刚才还在喧闹的风啊,鸟啊,孩子们啊,一瞬间都不见了,让人疑心,这世上的很多东西都跟上河水走了。
没有风,却觉得有一种空寂的冷,从河水里升了起来。奔波在外的人们赶回家时,月亮已经挂在河湾上。
河水古老,人不过才来这里几十年,依傍着河,生着,活着。
前些年,夏天的雨水一大,荒原就会发山水。浩荡的水掀着浪,咆哮着,不顾一切地向着黄河奔流。可是,半路上,那些水却流不动了,停了下来,开始向四处漶漫。黄河已经那么近了,它们就是流不动了,让奔跑着看山水的孩子伤心一场。
黄河在这世上流了那么多年,背负着那么多的东西,满河的泥沙在拽它,岸边的草木在拽它,地里的庄稼在拽它,活命的人在拽它……它一路挣扎,一路奔突,穿过无数山川,无数沟壑,无数城乡,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黄河怎么能停下呢,它在太多太多人的命里活着。
这一个一个的人,他们的命运,孤独与爱,与河紧紧相连,一同起伏。河给予了他们,回应了他们,安慰了他们,也在他们心上留下了伤痕。
河岸边,气象更迭,苍郁依旧。
二
病中的母亲,总是会说起农场。
母亲的眼中飘荡着回忆的雾气。那时候,她年轻,每天要去黄河岸边的农场劳作。她喜欢农场,四处都是荒凉干燥的矿山,只有这一小片农场是湿润的,像荒野里的一个梦。路很远,如果赶不上车,就要独自在沙地里走上两三个小时。
在农场劳作的人,都是被命运抛置在这片荒野里的人,他们在风沙中挖出一条一条的水渠,把黄河水引向更大的荒地。他们的身体里,除了漫天的大风,就是黄河水。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才回到家,她回来的时候,我在睡梦中。早上睁开眼睛,母亲已经走了。我的手边,放着一个金黄色的甜瓜,梦里边,是彻夜的香气。
我和母亲说起那些甜瓜的香气,夜晚温暖的谜。她笑了,你会记得这些,那时候你那么小。
母亲常常游离在时间之外,她的身体里充满各种记忆,各种时刻,有时候突然说起什么,整个人仿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河水涨了落了,果子熟了,叶子落了,能从冰上走了。许多的乌鸦,停在河岸边的沙枣树上,一动不动,突然叫上一声,会把人吓一跳。母亲说,农场的地真是好呢,长出来的黄色西红柿,一个柿子就可以切一盘。
黄河里的鱼特别多,人们休息时,跑到河里抓鱼,放在河岸边挖开的沙坑里,收工的时候再带回家。母亲说,她记得有一条金光闪闪的鱼,这么长,她用手比画着。沙坑里的水渐渐干涸下去,那条金色的鱼看着母亲,无望地张着嘴,母亲抱起鱼,飞快地把它送回到河水中。
母亲忘记了,农场已经消失了。但她记得河,记得岸边的草木,果实,沙枣树上的乌鸦,河里的鱼,秋天寒霜中冻死的蔬菜。它们和她一起接受了河水所有的恩赐。
我轻轻地抱着她,听到河水在母亲身体里缓慢地流动,时间没有让这些水声断流,它们正在从她的身体里向外奔流。
母亲说,你要把那条鱼放回水里。
我不知道她是呓语,还是认真的,我点着头,握紧她的手。那双在黄河里泡过无数遍的手,粗糙,干裂,布满细纹,有着泥土的味道,河水的味道,青草的味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一日一日地糊涂起来,每一样东西都在离开她,像一条一条的鱼,奔向河流。
我去了鱼市。
一条金色的鲤鱼,在水盆里激烈地扑腾着,旺盛的生命力,毫不妥协的挣扎。摊主说,这条鱼是野生的,现在人们都吃不到野生的鱼了,早上才打回来,你多幸运。
是的,幸运。我相信,这条鱼就是母亲和我说起过的那条鱼。

八月的黄河,宽阔平静。
手伸进水里,河水是温热的,暖和的。
我把鱼小心翼翼地放进水里,它迟疑了一下,又往深处潜了一下,仿佛是在试探,然后迅速地潜了下去,鱼尾巴轻快地甩出一个很大的弧。溅起的水波不断向四面散着,一层层晃过来,荡过去,水面上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该祈祷什么呢,鱼儿,你走吧,把人世的苦痛都带走,把母亲留下。
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走后的每年秋天,我都去黄河放生。我想,总有一条鱼会回到母亲身边。
三
年轻的父亲独自走在冬天冰冻的黄河上。
那时候,黄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没有公路桥,渡轮一进冬天就早早停了。因为着急,父亲等不上第二天才会开来的火车。
父亲对这条河并不陌生,他常常跟随着矿山马车队来河边拉水。从矿山到河边并没有路,只有方向,去时候走出来的路,一场风过去,回来的时候,什么踪迹都看不到了。马车拉着水就在大大小小的沙包之间穿行,父亲小心地听着那些水在罐子里的撞击声,生怕它们会漏出来。再混浊的河水也是珍贵的,用明矾清澄几日,就可以食用了。冬天,马车队的人们会刨下大块大块的冰运回去。矿区的人们闲下来的时候常说,哪天过趟河看看呢。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一年也过不了一趟河。
我长到十几岁,才第一次过河去看了看。
从不准时的渡轮上载着货车、公交车、自行车,满脸灰尘的疲惫的人们。遇到河水涨了落了,机器故障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渡轮就会停渡。一天漫长的等待全部落空。
人们守着河,但也惧怕着河,怕它神秘的力量,莫测的性格,突然的暴虐。春天开河的时候,河面上的冰块慢慢爆开,互相推挤着,碰撞着,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河不再有往日的平和,它变成了一条狂暴的,毁灭性的洪流,向四面冲去。住在河岸附近的人,还在睡梦中,就被河水带走了。
我不知道,父亲走在一条凶险的冰河上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也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矿山人像父亲一样,为了赶路,冒险走过冬天的黄河。
即使是冬天,黄河内部依然有着无法停息的生长与消亡。

父亲听到白茫茫的冰层之下,有水流在窜动,互相挤压,偶尔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一声钝响,也许是哪一处的冰裂了,也许是一块冰落进了水里。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父亲紧抓着一根岸边找来的树枝,用力地敲击着前方的冰面,向前慢慢探着,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树枝重重地落下去,有细小的冰屑随之跳了起来,每一片,都被月光放大了无数倍。头顶是白色的星星,地上是白色的冰晶,月光和冰河共同构筑的边界,无限延伸,一片白色的雪原。
如果树枝敲到的是一块薄冰,冰会顺着重力四面裂开,因为寂静,空旷,那声音显得格外响亮,带来了所有的想象,仿佛四面的冰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裂,有什么东西正在打开。
巨大的未知的恐惧令父亲陡然升起寒意,他犹豫着,迟疑着,细密的汗水瞬间涌出。父亲觉得自己与这些恐惧凝结成了一块冰,在河的中心,在世界最薄的边缘。
月光把河照得通明剔透,安抚着这个站在河中心孤立无援的人。
月光落下来的声音,砸在冰面上,一下,一下,像父亲的心跳。那些光落在父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一层坚硬的、透明的铠甲,在黑暗中闪着光。
父亲终于跨过冰面,站在河岸边,他没有回头望,甚至都没有停。
父亲背后,一片辽阔寂静的月光。
四
这座城市的第一座桥,是穿城而过的包兰铁路线上的跨河大桥。
那一座桥,和他有关,他曾经是一名守桥战士。
多年后,我问起这段往事,他神色怅惘,只是说,每天就看着火车从黄河上穿过,黑色的煤车,绿色的客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不用想象,我也熟悉那些场景,去河边看大桥,是我们童年时候常做的事。
大桥高出河岸很多,他站在悬空的荒凉的无人地带,雕塑一样,被河面上的大风日日吹着。桥下永不停留的河水,等火车的人,看大桥的孩子。
他听见自己年轻的孤单的骨头,发出树枝断裂一般的声音。
夜晚,远处的荒野都变成了浓重的黑,除了干涩的冷风,只有星星和远处一些零碎的灯火。又一列火车呼啸着过来了,车灯在黑暗中像两只巨大的眼睛,逼视着他。灯火通明的窗户,去向远方的人们,他突然觉得自己被这世界忽略了,被挡在了世界的外面,无法参与无法进入。有什么东西从他心中像河水一样狂奔出去,消失在茫茫暗夜。
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早已回到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家乡。可是这座铁路桥,却像人生中不多的无法清晰表述的事,总在他心里亘着。
他再一次回到这里,那座铁路桥已经变得破旧不堪,被废弃,被遗忘了。桥的上游和下游分别修建起了壮观雄伟的新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河也变成了湖,黄色变成了蓝色,那么鲜明的界限。黄色和蓝色,泥沙和清水,各归其位。
几十年,也可以是沧海桑田。
桥北边的双车道公路不断传来车流声,各式的客车、货车不停地过来过去。南边的新铁路大桥上,一列火车正疾速穿过黄河,不再是他熟悉的绿皮火车,不再冒着成团白烟,不再有惊人的响动。那些白色蒸气像彗星的尾巴一样闪耀着,旋即消逝在无边无际的虚无中。
旧铁路桥面完全锈蚀了,岗楼窗户上的木头板条被人拆去,四壁豁然,一只空洞的眼。高高的钢梁架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桥下的河水孤独而单薄,裸露的河床让人难以相信它曾经咆哮着席卷万物而去。曾经的沙枣林也不见了,几棵零星的沙枣树站在黄河水里,以一种哀悼的姿势。
他的回忆一时间混乱起来。
他想起那些年的冬天,经常下雪。那些雪真是大啊,黑暗之中,他都能够看得清雪的形状,薄薄的一片,嵌着微小的颗粒。雪花落在河面上,雪花落在铁桥上,雪花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睫毛上。大雪让世界陷入沉默,河流都不再发出声音。他害怕自己被冻住,消失在一场大雪之中,而他,还没有爱过。
这么多年,他睡在河水那样深的夜里,常常会梦见汽笛的鸣叫、疾驰的火车和将至的大雪。梦里,他也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看守大桥的战士了,但他多么想和那个年轻的自己再次融为一体。
他独自一人,站在大雪中,和一座桥在一起。
那些落在大桥上的雪,落在河面上的雪,它们一直在他心里落着。

五
城南的黄河中心,曾经有一个岛。
岛是由七个相连的小岛组成的,其中一个岛上长满了胡杨树。胡杨种子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河岸边没有见到这种树,它就奇怪地长在河水茫茫的岛上。
胡杨并不是常见的树种,人们就把这些岛叫胡杨岛。
几个岛之间相距不远,枯水季节,水落下去后,会露出一片沙地,人可以徒步在几个岛间往来。涨水时,牧羊人就把羊撒放在岛上,十天半个月也不会来一次,羊们在岛上自得其乐。
后来,他来岛上建设旅游区,人们把他戏称为“胡杨岛岛主”。
他一个人在岛上待了十七年。
那些年里,岛很是热闹,这样荒凉的地方,总还是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去处。
我去岛上的时候,岛已经不对外开放了。这座城市正在进行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水位抬高以后,岛将会被淹没。
岛主和两个一起来的朋友收拾着岛上的东西,有的要卖,有的送人,有的带走,有的留下。
我独自在岛上乱走。岛很大,到处是各种草木,突然从树丛中飞出来的一只颜色艳丽的鸟,呱呱叫着,倒把人吓一跳。
一个人的岛,多么奢侈。
他有一万棵胡杨树,一万棵沙枣树,几千棵沙棘、冬青、四合木、半日花、野枸杞……一百只羊,三头牛,还有无数的野兔、野鸡、松鼠、喜鹊和麻雀……
他比全世界都生机盎然。
一片灰绿色的沙枣树中,蓦然出现一棵巨大的胡杨。我仰视着这棵胡杨,一位正在巡行的国王,戴着金色的王冠,持着金色的权杖,光芒闪耀,让整个空虚的天空都震颤起来。
这样的美会让人对生命生出无限感激。
突然想到眼前的这棵树,眼前的这一切,在不久之后,都将沉于水下。一种窒息感随之涌了上来,不能太饱满,饱满就会破碎,像一个肥皂泡。
饭是在岛上吃的。岛主用各种野菜做出美味,葡萄酒也是他自己酿的,放了玫瑰花,清亮的红。他兴致还好,说起各种往事,在岛上建房子,筑路,各种劳作。冬天的时候,河水漫上来,和胡杨冻在一起,他就碎冰煮茶,烧木柴,在房间里作画。他说早晨起来,看见胡杨树上分泌出的树脂,晶莹圆润,像是树的眼泪。喝下去,那味道是苦的,他能感觉到那苦沿着他的四肢蔓延。
没有人说以后。
天色渐暗,暗下来的光线慢慢开始膨胀,并逐渐扩大。突然之间,天空中金光漫涌,像是有人在岛上点了一把火,大胡杨树热烈地燃烧起来。
他不再说话,失神地看着那棵大胡杨,他看树的眼神,像看一件遗物。
光只停留了片刻,然后,岛上的一切都变成了影子,变成了灰烬,变成了黑暗。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岛屿周围,一片茫茫的水,加深了夜晚的孤独。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没过多久,就听到他过世的消息。
他没有看到淹没后的岛屿。
我也没有去看淹没后的岛。尽管我会好奇,大水中的胡杨,是否会一直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像站在沙漠中一样,千年不倒,千年不朽?
关于胡杨岛,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个黄昏,一棵巨大的孤独的胡杨树的美。
六
他是我在矿区中学时候的美术老师。
他给我们讲美术史时,会用幻灯机放映图片,有世界名画,还有雕塑。
放映大卫或者维纳斯的时候,一些男生故意哧哧地笑起来,有的女生就忸怩不安地低下头去。他不看我们,继续停留在他的声音里,他的讲述里。
阳光洒进教室,满屋子的灰尘上上下下地飞舞着,他的手掌不断地伸向空中,明暗之间的手指闪烁着愤怒的难言的孤寂之痛。他的眼神停留在某一个空茫之处,或许只是一粒让他着迷的灰尘,他对着它们说话。
痛压迫着人,让人彻夜不宁。
课余,他穿过校园附近破旧的土坯房,向着河走去,河在那里等他。他觉得,河向他发出了某种召唤,未知的召唤。
河边到处是一块块被河水磨圆的黄河石,他捡起这些石头,仔细观察着石头上精美的花纹,河流也是艺术家呢,它们把平凡的石头塑造得如此之美。可是,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徒劳的,然后用力把那些石头扔进河里。石头在水面上划出动荡的水纹,随之沉入水中。
他俯下身子,尽量让自己离河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内心的灼痛无限地贴近河。他清晰地在水中看到自己的脸,苍白,凝滞,像那块掷出的石头,在河水里缓慢下沉。身体和灵魂之间突然出现的陌生分离,让他产生出莫名的惶恐和不安。
他沿着河岸不停地走,他想走得更远,更远。
他离开学校,用了一年的时间,徒步从黄河的源头走到了黄河的出海口。
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没有人知道,他的身心承受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折磨和击打。他的头脑被各种思绪,想象和突然出现的疯狂的想法所塞满,内心的丰盈、激动和痛楚几乎要撑破每一秒钟的时间。
他把自己想象成受难者,圣徒,他坚持到了最后,完成了自己。
黄河清空了他,又给予了他,他成了著名的画家。他想,他终于被这条河治愈了。
要到多年后,他才会了悟,他并没有被河治愈,河给了他更大的孤寂之痛,追寻之痛。他画了那么多贯穿他生命的河,让他九死一生的河,他却觉得他并没有画出心里面的那条河。
一直以来支撑着他的坚固的东西开始崩塌,原来被遮蔽的被忽视的或者说是被他刻意忘记的一些东西,慢慢回到他的意识之中。也许,他走得太远了。
未完成的美,会成为一种隐匿的痛,蛰伏在身体的内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浮上来,把他再一次拉回到黑暗之中。
七
她沿着河岸,寻找一座桥。
那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公路桥,建成那天,整个城市欢腾不已。从此,人们不用再等待渡轮,等待火车,不用再月夜渡过冰冻的黄河。
人们都觉得桥是重要的,联结着远方,联结着世界。她却觉得,河才是重要的,河能抵达很多地方,但桥不能,桥只能站在原地。她是一个冷淡疏离的人,从不和同学往来。小时候,她的父亲在井下砸断了双腿,到上海治病疗养,母亲长年在上海陪护。她一个人带着弟弟妹妹留在这里。
初中都没有毕业,她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许多年后,她再回来,所有熟悉的地方,都变成了巨大的陌生之地。
她无法相信河水中间,那座桥墩一样的东西,是曾经的公路桥。
那座曾经让万人欢腾的公路桥,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部分中间桥身。没有头,没有尾,桥以一种怪异的残缺的姿势立在水中,像一段没有来路没有去向的记忆,既不开始,也不结束。
她远远地看着那半截桥,像看着一个残缺的伙伴,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无助地站在一片大水中,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悲伤。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桥的委屈,也是她的。她一瞬间冲动起来,想跑到桥跟前,抱着桥大哭一场。
桥四面都是水,把桥和她远远地分离开来,她无法走到桥的身边。桥的无法抵达,让她的回忆她的过去一时间变得无所依附,无从说起。
她经常会一个人躲在河岸边的桥洞下,四面有很高的茅草,隐秘安全,安放了她所有的悲伤。
她在大桥下躲过一场雨。
那时候,太年轻了。不知道,下雨,河水会涨,不知道,一场大雨也可以把一个人淹没。
四面的雨点飞快地落入密集的水流中,瞬间便被水流吞没。河道动荡不安,横冲直撞,河水在迅速地溶解一切,让一切消失。
河水缓慢地上涨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正在慢慢生成,或者是正在释放。她没有丝毫的恐惧,平静地看着河水的上涨,仿佛在等待着身体内的力量,等待着那些力量从河水中浮现。
雨停了,像来时候一样突然。
岸边的草木别样的明和亮。河对岸的甘德尔山飘起了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山的颜色由荒芜的灰褐色变成了湿润的苍青色。一道彩虹挂在山间,确切地说,是半道,彩虹的一侧被云朵遮住了,但它依旧是完美的,神奇的。一只白色的大鸟突然从草丛中飞出来,抖动着身上的雨水,白鸟的翅膀闪着奇异的光,缓缓地从她面前掠过去,穿过黑暗的桥洞,飞走了。
她经受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一切,像一个跋涉了很久的人,找到了歇息地。整个人放松下来,紧紧地抱住自己,泪流满面。
异乡的夜里,她会清晰地记得那个遥远的下午,上涨的河水,黑暗的桥洞,彩虹,白鸟,她与命运的冲突和化解。
河水一路向前,从不会为谁停留。
只有桥,停留在原地。
尽管,桥已经不再完整,残缺和割裂让它变得甚至不再像一座桥。但是,只要桥在,她就不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停留在原地的桥,坚持着和时间形成某种对峙,把她过去的痛和逝去的青春全部还给了她。
八
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我正在壶口看黄河瀑布。
电话里的同学语无伦次地说着,哭着。
他和几个人在黄河里电鱼,其他人都没有事,只有他触电而死。他是第一次和别人去电鱼,他平时连鱼都不钓的,他只是想找个方式喘息一下。
他怎么会死去,以这样荒谬的方式,有一刹那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像是谁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放下电话,沿着河岸走,壶口瀑布巨大的轰鸣声中,水花不断喷溅到我的脸上,一脸的温热。我茫然地看着眼前不断流过的黄河水,气势万丈的壶口黄河水,它们流到我居住的城,已经变得平和,缓慢,可是,它们还是带走了他。
人的生,人的死,河见过太多了,这世上的聚散离合,一刻不停。
一个男人从刚刚建成的大桥上跳了下去。那是冬天,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那个男人就那样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要有怎样的悲痛和绝望,才会这样不管不顾呢?
这么壮观美丽的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死亡前的平台。
还有多年前的一对情人,僻静的河岸边,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没有一物可以隐藏的荒凉之地,是河安放了那些慌张的情欲,软弱的肉身,但也是河带走了他们。河怎么会不懂,人世间纷纷的情欲,并不比岸边的一株茅草更茂盛,比飞掠而过的一只白鸟更孤寂。
这些人,都有一个死的理由,而他没有,他刚买了新楼房,他还没有住进去。
他每天穿梭在城里众多的建筑工地,一早一晚都要经过大桥,有时候会看到太阳升起或者落下,更多时候看到的是满天星星。吹到他脸上湿润的河风,都是苦涩的。
河边有人在漫步,有树在生长,有花在开放,而他,被这条河带走了。
他躺在河水中的一刹那,有一种失重的漂浮感。他第一次感受到这条河的广阔,河水的温暖和起伏,他在这温暖里漂流,像河面上的一片苇叶。他心里升起一股奇异的哀伤,他还不曾好好地看过这条河,不曾看过早晨河面上轻纱一样的薄雾,黄昏时让人落泪的长河落日,春天里壮观的流凌,还有夏天长满了各种草木的滩涂湿地。
云层很低,贴着桥面飘了过去,云朵的阴影覆盖在他的脸上,像是神的手掌,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抚摸着他始终皱成一团的心。
河上的云彩真美呵!
他在奔流的水中,终于松开了紧紧攥住的手,沉入一片虚无的蓝色,空洞迫人的蓝色。
河水打着旋涡回到安静。
他就以这样荒诞的方式死去了,也许死亡本身不荒诞,生才荒诞。
没有人再说起他,河水平静地带走了所有属于过往的事物。
九
我一直记得新大桥上的一幕场景。
神情肃穆的一家人,站在桥中央的栏杆边,抓着罐子里面的骨灰,一把一把洒到河里。
他们是希望骨灰随着河水,一路飘荡回老家吧。也许,哪里也不去,就是想和黄河融在一起。
父亲生前也有过死后埋在老家的念想。父亲去世后,我们把父亲埋在能看得见黄河的一片墓地里,河会把父亲的念想带回老家。
祖父从陕西的黄河湾,迁徙到河套平原的杨家河,父亲又从杨家河来到乌达。父亲一生都没有离开这条河。
许多人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条河。
河流将时间的意义确立,将人的命运确立,也让我得以确立自己生命的支点和重心。
我去过贵德,那里的黄河水,清澈,碧绿。我把手伸进去,我血液里的水分子就知道了,这不是我的黄河水。贵德的水那样清亮,那样明媚,像一个天真快乐的孩子,还没有经历辗转,沧桑。而我的河水混浊,昏黄,泥沙俱下,我的身体里血液中携带着河的因子、精神和情感,那些孤独,沉重,温暖和力量,终生都会存在。
河日日都在变化中。
长长的新大桥,在夜里会亮起绚丽的灯光;岸边,大片大片的绿地,女孩子的裙摆掠过明媚的花田;孩子们在水边奔跑,欢笑,用手里的面包屑喂着成群成群快乐的红嘴鸥……
这一切都让我眼眶湿润。
我看见母亲在农场的菜地里,深深地弯下腰去,看见父亲从黄河的冰面上走过,他背后的那片月光好白啊,像父亲的脸……
刊于《草原》2022年第3期

刘惠春,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乌海市。作品散见《短篇小说》《作品》《草原》等刊物。出版散文集《我们像风一样活着》。
创作谈
一个人的河流
/ 刘惠春
黄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奔腾在大地上的河流,它还是一条被说出的河流,被写出的河流,即使河中的一粒沙、岸边的一株草,都被从众多的角度描述过解读过。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写这条河呢?
缘于一次偶然遇到的场景。
一天,我坐车经过乌海黄河大桥时,看到一家人,戴着黑纱整整齐齐地站在桥边,一个年迈的妇人抱着一个骨灰坛,正一把一把往黄河里撒骨灰。无论是老人的遗愿还是家人的意愿,这一幕都让我深感震惊。神情严肃的儿女们,看上去和我同龄,他们的父母应该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异乡人。他们来到这里,亲手建设了这座城,然后在这个城市老去,把骨灰洒在了黄河里。
我的眼睛突然涌出了泪水。
那一刻,我特别想知道,对我们的父辈来说,对我们这些这座城市出生的第一代人来说,对河岸边生活的一个一个人来说,这条河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所在的城市乌海,建市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第一代创业者从全国各地而来,把自己从根上折断,在这片一无所有的荒原上,开枝散叶,开辟家园。几十年间,流经乌海的黄河上前后修建了五座铁路桥、公路桥。桥与桥之间,与河流相连,与生命相连,与城市的建设相连,与时间相连。
我看着这条河,不断地回忆它,融入它,成为它,那些过往的时光,那些辛苦存活的人们,那些从未被讲述过的事物,那些缓慢生成的根系感,慢慢从河水中浮起。
我远远无法用定义和词语来描述这条河,也无法把更多的意义附加在它身上。我只是一再审视记忆,还原彼时情境,从中提取出不同时间段的河流样貌和迥然不同的叙事片断,去重现那些瞬间,回应那些情感。我希望这种努力,像一个切片或者刨面,能够呈现出河流之上生命的图景,以及人与河之间紧密而深刻的关系。
黄河并不是只存在于人们的生命之外,时间之外,它是人们情感的依托,精神所向和灵魂长涉。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的意义,它都始终在延续在流淌,在所有人的生命里流着,也在所有人的回忆里流着。黄河散溢成岸边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所有人又共同叠合成一条宏大的生命河流。
黄河日夜流淌,波澜不惊,河岸两边早已不是旧时模样。过往的岁月不过是河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出现,然后消失。但是,消失,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存在过的事物会永远存在。
春天来了,冰层之下的河水在激烈地涌动,岸边的种子在萌发,水鸟们从远处飞来,河面上青蓝色的雾气在荡漾。
身边有这样一条大河流淌,何尝不是安慰。
爱一条河流,更接近于爱的本源。
版权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机场南辅路5.5公里处
电话:0471-4934352传真:0471-4925404
投稿邮箱:nmgwlwycbz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