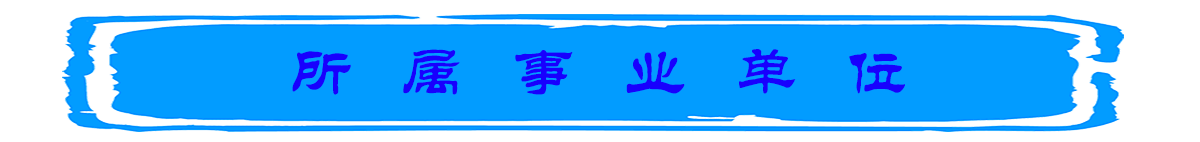
来源:内蒙古文学杂志社 时间:2023-09-22 14:22:09 阅读量:
9月19日,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内蒙古作家海勒根那刊发在《草原》的小说《巴桑的大海》荣获中篇小说奖。
海勒根那的小说《巴桑的大海》刊发于《草原》2021年第4期“特别推荐”栏目,后经由《小说月报》转载并入选《小说月报2021年精品集》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获奖感言】
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
【获奖作品】
《巴桑的大海》

刊发于《草原》2021年第4期“特别推荐”栏目

《小说月报》转载并入选《小说月报2021年精品集》

入围《收获》杂志“2021年收获文学榜”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推出单行本
【名家点评】
《巴桑的大海》

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月报》《散文》主编 汪惠仁
海勒根那的写作,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在将《巴桑的大海》收入“百花中篇小说丛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巴桑和我们的区别是那么大,他被抛到人世间,迎接他的是一个又一个厄运,人间悲苦集于一身,却能一直向阳而生。这让我想起曾经遇见的一个在风景区牵马的藏族女孩,她父亲早逝,弟弟被马蹄踢瞎了双眼,年幼的妹妹需要照料,她从大学辍学回来支撑着这个家。她的心中岂能无悲苦,但她没有向困厄的命运低头,她解决着一个又一个人生难题,最终奇迹般地向着阳光生长。我想,这也是巴桑的故事的感人之处,而且巴桑的故事更撼人心魄。每一次困厄到来,巴桑都获得飞升。我们的写作缺少神启或天启的力量,而海勒根那给了我们巴桑,给了我们向光向善生长的人生案例,给了我们神启或天启的力量。
著名文学评论家 孟繁华
《小说月报》对中篇小说的重视,以及诉诸实践对其进行弘扬彰显,是非常有眼光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例。我认为中篇小说的门槛越来越高,是百年中国最有成就的文学文体,获得了学界的认同。
海勒根那是这个时代重要的小说家。他和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范稳等作家一起书写和呈现了中国文学的边地经验,提供了新的边疆和民族文化的知识、思想和情感,拓展了当下小说的版图和边界,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增添了新的元素。他的《到哪儿去,黑马》《寻找巴根那》《骑手嘎达斯》《骑马周游世界》《小黄马》等作品,在读者和评论界深受好评。《巴桑的大海》延续了海勒根那小说主题的某些部分,就是对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认知、理解和面对。海勒根那这一主题的提炼,不仅仅来源于他接受的教育、民族文化的熏染,更来源于他个人的童年创伤记忆。
小说命名为《巴桑的大海》,讲述了巴桑从草原到大海的艰难历程,但这只是小说表面的能指。这里的大海,更是一个隐喻或者一个比喻。这个大海是巴桑的胸怀、情怀和无疆大爱,是一个没有被后天伤害打倒在地的英雄,仍然可以劈波斩浪纵横驰骋于爱与善的海洋之上的一叶飞舟。
著名文学评论家 贺绍俊
青年巴桑是一名让人惊叹的草原硬汉,他在失去双腿后最想要做的事情竟然是要去看大海,还要走遍全世界。巴桑凭着坚强意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在想,海勒根那为什么一定要将巴桑设计成失去了双腿呢?难道就是为了强调巴桑所做的一切特别不容易吗?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在我看来,海勒根那是将残疾作为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考验来写的,他表达了对残疾的一种认知,表达了他的尊重和关爱。由此我想起了作家史铁生。史铁生的双腿失去行走能力,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也像巴桑一样,并没有被残疾所击倒。史铁生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比如他想走却不能走是一种局限,而健全的人想飞却不能飞也未尝不是一种局限。史铁生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局限,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超越局限,让生命更加精彩。史铁生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比我们这些腿脚健全的人行走得更远。很多人虽然身体健全,却无法达到史铁生的精神境界,相比于史铁生,这些人可以说精神上残疾了。
海勒根那是一位有着悲悯情怀的作家,他写了在巴桑身边的许多好心人。即使对待心智残疾的布仁,作者也宽宏大量地给了他觉悟的机会,当巴桑要去马戏团时,布仁悄悄送给了巴桑一把轮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作者补上这一笔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善良和温暖的一笔,这也是这篇小说的底色。
【创作谈】
《巴桑的大海》
巴桑,另一个自己
海勒根那
怎样使小说读起来不费劲,就像看电影一样,悬念迭起,引人入胜,这是个让码字的作家最伤脑筋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像福克纳那样自说自话,不管你看没看懂,也不管你困不困觉。可很多时候,我读小说就像听催眠曲,哪怕是鼎鼎有名的大师的作品,读不上三段就昏昏欲睡,尽管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所以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就连写小说的读小说都会睡着,那让普通读者情何以堪?这样下去,我怕“读小说”这种本就不合时宜的消遣方式哪天真的因为越来越不好玩而被束之高阁。这般担心并非多余,所以我近两年的小说尽可能写得好读,最起码故事开头做了这样的努力,预设一根线拽着读者读下去。《巴桑的大海》的开头就是这样——“我跑长途做运尸人那些年……”
这是小说为了吸引读者玩的花招。卡佛说,小说家最好不要耍花招,但他同时也说“一个短篇里要有点危险感和紧张感,有助于避免沉闷。”对此我的理解是:危险感和紧张感不属于“花招”,这样我就安心了。巴桑的故事可以平铺直叙吗?当然可以,但故事跨越的时间有点长,一个人从小长大,从生到死,让大家从头看到尾,确实难为读者,确实乏味,虽然他的一生足够曲折离奇。
但写巴桑的动因却是因为别的。有时候,一篇小说可能来源于一幅画面,一个场景,一段音乐,一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即便鸿篇巨制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自称他的灵感也仅仅来自于一个视觉形象——某个午后,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去见识冰块,这是马尔克斯珍贵的童年记忆。在他小时候,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把冰块当宝贝展览。有一天他对外祖父说他还没见过冰块,老人便带他去香蕉公司的营地,打开一箱冰冻鲷鱼让他把手按在上面,让他感受一块冰的温度,从而为马尔克斯的童年铭刻了深远的记忆。而余华创作《活着》时,据说是他听了一段美国民歌《老黑奴》……这里,我无意拿自己与大师相提并论,想说明的是写巴桑其实只源自我的一个心结,它与我的童年紧密相连,那就是失不复得的父爱母爱。几年前我为父母亲修缮墓地刻立墓碑,才确切地算出父亲和母亲其实是在我四岁和九岁时去世的,而我则是从九岁开始便流落于几个姐姐、哥哥和叔伯家,尝尽了人间的辛苦。我不知道“孤儿情结”在心理学中有没有相关论述,它对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哪些影响,总之它影响到了我,冥冥中呼之即来,却挥之不去。我为此写过小说《父亲鱼游而去》《母亲的青鸟》《我的叔叔以勒》等等。不过,在写巴桑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遗忘了童年,因为很少在梦中与之相遇了,要知道我现在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儿子也比当年失去父亲时的我大上两岁。可就在我做梦都梦不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又向我发出呼唤,就像《河的第三条岸》里的父亲,在永不上岸的小船上,在故事的最后,还要向主人公招手示意。
其实更多时候,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都缺乏归纳。当有一天评论家指出我多篇小说的共性时,我才有所察觉,他们说,你的小说里怎样那么多“出走”和“寻找”,你的困惑到底是什么。为此,我找来这些小说,找来《寻找巴根那》《骑手嘎达斯》《温都根查干》等等,左瞧右看,发现评论家言之凿凿,但我却无从知晓自己内心的隐秘,是蒙古人的基因作祟,还是童年四处沦落的结果。是的,蒙古人自来没有固守的概念,他们生来便逐水草而居,有蓝天的地方就有信仰,有草原的地方就是故乡。记得几年前,我曾经犯过一个幼稚的错误,根据家族传说去寻找自己的祖籍——察哈尔正蓝旗伊和苏木,我从呼伦贝尔出发,跨越兴安岭、科尔沁,去往锡林郭勒,在浑善达克沙漠的边缘,我放大了卫星地图,试图找到祖先曾经的居留之地,事实上,如今的正蓝旗伊和苏木因撤乡并镇已不复存在,而整个锡林郭勒叫作伊和苏木的地方又比比皆是。面对这种魔幻般的现实,我的寻找注定无解。后来当我读到一本介绍蒙古各部之源流的书,我才感到了自己的愚拙:自蒙元以来就担负皇家卫队职责的察哈尔部,所踏过的足迹又何止蒙古高原,即便有故地也是短暂驻留,我们又该怎么定位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换言之,草原如此辽阔,一条河和另一条河如此近似,一座山和另一座山这般相像,蒙古人又该怎么区分哪个是家园哪个是异域?
这么说,该是游牧人的“出走”和“寻找”以某种遗传的形式流淌于我的血液里了,并在我学会写作后不自觉地显现出来。虽然我的“出走”和“寻找”其意义已不同于祖先,包括这次启程的巴桑。
其实在巴桑走向大海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要去向哪里,总之我要让他代替我再次远行。那些天我无意中听到了一首草东的摇滚歌曲,其中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一句:……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转身向大海走去……这无端的歌词反复萦绕在我脑海里,仿佛在暗示着巴桑——这个在内陆草原长大的孤独少年,因为对父亲的渴慕,因为对远方的想往,最终走向了大海。为了让故事有更大的落差,我假设了这个少年没有双腿……这个情节并非我无中生有,凭空捏造,那是另一个牧人的故事,他年逾五十,就居住在哈拉哈河边,因捡拾诺门罕战役留下的一枚炮弹而失去了下肢,现实中,他的一个伙伴也躯体全无……战争留下的“遗产”从来都没有消失,给人类留下的隐痛也无处不在。当巴桑的形象在小说里渐渐清晰时,他也有了生命和人格的温度,他向往父亲般的伟岸和大海的宽广,但他更同情弱者,悲悯生灵,并且可以为之付出一切。
巴桑最后身葬大海,这是我为他预先设计的归宿。只有这样,巴桑的一生看上去才显得适宜,才显得壮观而美丽。

版权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机场南辅路5.5公里处
电话:0471-4934352传真:0471-4925404
投稿邮箱:nmgwlwycbz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