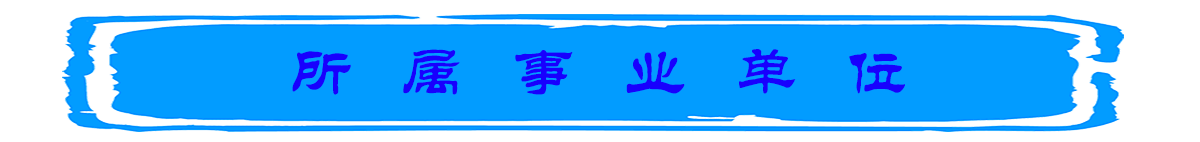
来源:内蒙古文学杂志社 时间:2023-09-22 11:37:54 阅读量:

悲情勇敢的孤勇者
——谈海勒根那小说的一个主题
赵筱彬
近读海勒根那的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还有他的新作《巴桑的大海》时,心里不禁响起了陈奕迅《孤勇者》的旋律。人生最难的就是对抗孤独,正因为难,所以对抗本身就带着孤勇者的气质。《孤勇者》这首歌的出现,传递着某种奇幻的色彩。当它像接头暗号般,从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嘴里哼唱出来的时候,散发着英雄主义的光辉,并日渐成为一种人间理想般的存在。海勒根那作品中渗透出来的精神气质和笔下的人物,无处不散发着孤傲、独特甚至是悲情的气息,就像卡夫卡《变形记》中描写的孤独是“一天早晨,从不安的梦中醒来,躺在床上变成甲壳虫的自己”一样,孤独就这样出现并被塑造了,也由此传递出了撼人心魄的力量。
孤勇者形象的塑造
海勒根那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孤勇者的主人公形象,这些形象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经过陌生化的处理和艺术加工,变成了史诗作品中“神”一样的存在。他们孤独、冷峻,从现实生活中走来,又超脱于现实。《过路人,欢迎你来哈吐布其》里像骆驼一样高大威武的不速之客“阿恰”,永远都神采飞扬,酒量惊人,吃肉技法娴熟,人们清晰地发觉他的吃相好似《蒙古秘史》中的“大巴鲁刺”。作者借用“阿恰”的出现,描摹了哈吐布其人崭新的生活图景。海勒根那也试图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像深夜呓语,那一队人马身着古代战服,披盔戴甲,浑身血迹,铁青着面孔,游荡在无数个深夜,只为寻找自己的子孙,并告诫他们“贪婪是恶魔”。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人,是作者找寻精神血脉的通道,他们踏破历史的尘埃,根植于作者的内心,也成为他奋力抒写的一部分。
回归现实,海勒根那笔下的角色同样勇敢,充满悲壮的色彩。《蒸汽火车呼啸而过》中的平安为了能够为心爱的女孩拾回那条被吹走的围巾,像堂吉诃德一样,与呼啸而过的蒸汽火车搏斗。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人生走向,也塑造了一段真实而又模糊的青春记忆。《能动嘴就别动刀》中,一个凶狠手辣的主人公形象在破碎的叙事圈套里逐渐清晰起来,甚至到最后读者都无法辨别事情的真伪。当然小说虚构的魅力也在于此,大成子已然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了一个孤勇者。把历史和现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巴桑的大海》中的巴桑,这个草原上的硬汉形象传递出来的是“人可以失败,但不能被打倒,肉身可以遭受磨难,但内在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巴桑以自己的顽强意志,突破了苦难的重重围困,并在广阔自由的天地间构建起了伟大的人间之爱。
这些孤勇者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标榜了一个作家作品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在情感的链接上打通了多维空间。海勒根那不断将自己作品的格局宏阔起来,突破了历史、民族、地域的重重围困,在精神层面获得了更加自由广阔的天地。
孤勇者的精神气质
在叙述方式上,海勒根那不断让自己尝试着走出舒适区,选择执拗得近乎偏执的方式。为了充分表达的需要,他执意凸显个人的偏爱,创作了多篇以大师的作品标题命名的作品,这一方面是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师致敬,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如《第三条河岸》取自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取自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的叔叔以勒》显然取自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十八岁出门打工》取自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午夜沉溺》虽在标题上没有凸显,却是作者以短篇形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致敬的作品。海勒根那从不吝惜作为粉丝的狂热,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与大师之间的时空对话,其间凸显着巨大的张力。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对峙状态,这或许正源自海勒根那骨子里那份孤勇者般的倔强。
在创作上,海勒根那极度彰显自由的意志,他的部分作品虽谈不上精巧完美的结构、丰满的人物塑造,却能在异质性的内容和情节上得以补充。因而读他创作的故事,更像是在探险。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奇人怪事。《我的叔叔以勒》中被整个村庄忽略的以勒,他总是蹲在房顶的鸽群里,像大鸟那样望着天空发呆。你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却能通过爱这条通道,捕捉到浓浓的暖意。《羊圈里的弟弟》中的达拉并不聋哑,却终日不说话,他选择与羊群生活在一起,在羊圈里像是弓腰行走的一只羊。灾难面前的互相拯救与抚慰,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温都根查干》里的朝鲁校长用木头打造了一匹木马,一匹神秘得如同《荷马史诗》中的木马,给久旱的土地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海勒根那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了《蒙古秘史》,并且部分情节和场景的设置也同样有迹可循,他的创作受到了民族文化的侵染,这也成为他精神谱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探险里,读者也在一步一步逼近海勒根那作品中的精神内核。
“父亲死了”和“最后一个”的精神困境
在勇敢的外衣之下,海勒根那的作品又充满了悲情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止体现在他作品中“父亲”身份的缺席,而且还在于频繁出现的“最后一个”的意象,让原本虚构的故事带着某种宿命的色彩。
“父亲”一直是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原型,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海勒根那在作品中不断强化“父亲死了”这一人生困境,其实也暗含着“父亲”这个角色在人生命中的意义。《手套》中的“我”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不得不放弃学业,和母亲一起顶门立户。《父亲狩猎归来》中,黑熊的闯入打破了农民原本宁静的生活,早已放下猎枪的父亲无奈之下扛起枪,与黑熊搏斗,结果被黑熊吃掉了。《脚印》中的放羊人巴秃,人们提起他的时候,总想起他死去的阿爸老乌力吉,那个从小就扛着猎枪的独眼巨人。海勒根那虽没有过多描写父亲死亡的场景和死亡后主人公的心境,却在轻描淡写中诉说着悲情,那是一种朦胧的、越沉淀越刻骨铭心的情感。
“最后一个”是一种故事讲述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原型”。许多作家都喜欢讲述“最后一个”的故事,有的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一个”,有的甚至直接以此命题,如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汪曾祺的《鉴赏家》、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等等。“最后一个”与人类本性中喜欢哀婉和悲伤的情调有关。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就提出了“最谐美之音乐必有忧郁与偕”的论调,其实也是同样的旨意。海勒根那在作品中多次提到“最后一个”的意象,《鹿哨》表达了面对生态保护的政策与原始的狩猎方式之间的冲突时,鹿部猎人对于生活方式改变的焦虑。作者用“最后一次狩猎”,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划上哀婉的句号。《寻找巴根那》中,拴马桩旁有一匹老得不能再老的马,那是巴特家的最后一匹马,其中提到的女萨满也是科尔沁最后一个萨满。作品在寻找的框架之下,是一个家族的记忆,是主人公对于传统游牧生活的眷恋。《最后的嘎拉》让“父亲死了”和“最后一个”结合在一起,当嘎拉作为草原上古老的职业运盐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的时候,它也就成了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父亲在最后一次运盐的途中跌落在盐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阿爸死后,从此再没有嘎拉。”这是对父亲的追忆,也是对逝去的生活方式的挽歌。
除作品外,海勒根那身上同样散发着孤勇者的气质。他凭借勇气、耐力和冒险精神,在创作中不断吸纳和创造,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骑马周游世界》无疑是他一个阶段的总结,而从《巴桑的大海》开始,他突破了民族、地域以及个人经验的种种局限,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格局,探寻人类的命运和人性的幽微,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写作疆域,也让读者看到了更加真切有力的作品。期待未来他能带给大家更大的惊喜。
刊于2023年6月2日《文艺报》

赵筱彬
,笔名筱雅,1987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内蒙古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内蒙古文学杂志社副社长、《草原》副主编。评论文章散见《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人民日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
版权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机场南辅路5.5公里处
电话:0471-4934352传真:0471-4925404
投稿邮箱:nmgwlwycbz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