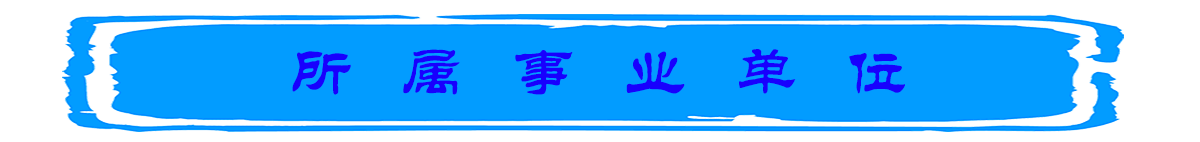
来源:内蒙古文学杂志社 时间:2023-06-12 21:46:55 阅读量:

写实与写意交融的
意象表达
——关于近年来内蒙古青年作家的
中短篇小说创作
文 | 韩彦斌
近年来,《草原》发表了一系列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有75后作家胡斐的《戛然而止》,80后作家晶达的《蓝胡子的邀请》、阿尼苏的《扎穆沁》、娜仁高娃的《醉驼》、肖睿的《筋疲力尽》、陈萨日娜的《一朵芍药一片海》、邓文静的《逃跑的牙齿》,90后作家渡澜的《美好的一天》、苏热的《黄塘记》、阿塔尔的《雪原战争》和00后作家田逸凡的《求你们告诉我》、晓角的《清冷之人》。这些作品带给我们一种非常独特的阅读体验,最直观的体验是作家似乎沉浸在自己的表达欲望中,将读者的阅读带入某种意境,并在叙事中逐渐把意境涂抹成一种感觉,或者说把感觉嵌入意境之中,使小说有意无意弥漫着浓郁的写意风格,小说的人物、情节、对话、动作、场景,甚至故事本身等成为构建意境的客观意象,使读者不能简单地按照以往的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的认知和习惯去阅读,否则将陷入作品极度内敛的压迫感之中,被紧紧限制在一个逼仄的“叙述胡同”内。它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有意设置的“叙述圈套”,虽然都造成了阅读的陌生化,但先锋小说的“叙述圈套”是有意为之,重在突出小说的叙述功能,作家置身事外,在意的是对素材、虚实等的处理。而内蒙古这批青年作家的小说带来的阅读陌生化没有明显的刻意而为,却能紧紧攫住读者的阅读兴趣,就像作家高度专注于一件事的叙述,读者也需要高度专注的阅读,并逐渐感受到作家的表达指向,才能渐入佳境而在颇耐咀嚼的审美体验中回味无穷。可能与一般情况下作家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同,这样的创作更注意的是自我的表达。这种表达以写实与写意相交融的方式将记忆、心境、物象,乃至故事本身设置为传达思考的意象。

内蒙古青年作家们
中国的叙事审美中多有意象表达的踪迹,既讲故事又借叙事抒发情感,形成关于人生哲学、精神寄托、情感言说、价值倾向等的美学追求。在作品中,往往表现为一种风格或理想的状态,因其更注重写意而非写实,使得书写把一切宏观或细微的事物赋予某种意象而植入文字中。正如高友工在《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所说,在中国叙述传统中,“现实与理想世界的排比,在叙述文学中,远较在抒情诗中复杂。但这些不同的悟解最终却可能被统合成一整体的境界……因而自然地暗设了一超越自我及现在的永恒。” [1]这些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向内的创作路径,营造出寄情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审美意象,“人”的现代性生成与传统意象抒情共同发力,展现出现代与传统互不拒斥的审美趣味、精神面貌和人生情致。《黄塘记》写了“我”在一次车祸后,去了距离家乡黄镇2000公里的南方小镇,一个谁也不认识我、我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在那里我打算以小说的形式写一部关于黄镇的历史。“我”需要回忆,或许是人生来就在骨子里注定的“鱼的基因和命运”。“很多事情不存在人的记忆里,但人总是能想起它。”小说开篇即说:“在每一个地面有土、天上有光的地方,黄镇人都逃脱不了黄镇的束缚。”“世世代代,乐此不疲。”哪怕“我”因为车祸失去了曾经的记忆,但“记忆的轻纱总是在我进行写作的时候被风吹起,露出了一些关于黄镇的事情”。表面上是为了写作,实际上是无以挣脱的“水塘”使然,“水塘”或许代表着每个人想要逃离的家乡,令人纠结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塘”。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要被困在水塘里,就像“我”一直在向家人、朋友打听追寻的黄堂一样,不论远离家乡多远,身上都会和家乡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人纠缠进执拗的探寻中。也许“我”就是那个“我”一直寻找着的黄堂,也许“我”不是黄堂,但不管是不是,“我”的记忆留在了黄镇和“惶堂”的时空里,那是“我”关于一个地方历史的所有记忆和追索。“我”用小说形式写的黄镇历史就是一部属于自己原始冲动的历史,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哪怕这个小说写成的历史只属于“我”而不属于它的记忆。黄镇和黄镇的人,黄堂和与黄堂有关的事儿等,都是“我”记忆里的意象,小说细节叙事非常细腻,但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似乎无意反映或表现什么,只是通过各种意象的组合把作家沉淀在精神深处的原始欲望激发出来,以个人的情绪体验表达一般的情感意志与审美感悟。

内蒙古青年作家们
巧的是,《筋疲力尽》也讲述了一个由于车祸而记忆受损者的故事,只不过小说运用了超现实的手法,将“我”的意外伤害转换成了意外收获。“我”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发现自己身上拥有了“替换”的超能力,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替换成喜欢的人,而且都是温柔体贴的女性。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开始“我”为拥有这份超能力感到痛苦,但后来与H小姐的相爱,让压在“我”内心的恐惧逐渐消失,为了能够和她在一起,“我”用自己的超能力为她替换掉了很多人,甚至不顾道德观念只为满足H小姐的贪婪欲望。当“我”看着这个城市全部是被“我”替换出的女人世界,一个“虚伪的美丽的”世界,心底的道德感再被唤醒, H小姐无休止地利用“我”对她的感情去满足她的私欲,最终激起“我”的愤怒而杀了她。“逃到了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地方,那里紧邻大海。海浪的声音仿佛是在一瞬间就夺走了我的全部力量。” “我”决定从这里开始新的生活。“我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渔民。再也没有‘替换’过任何一个人,我很幸福……”但警察还是找到了“我”,“我”被判处死刑,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我”竟然无比享受地闭上了眼睛。然而“我”并没有高尚到接受道德或法律的审判而完成一次救赎,依然运用自己的超能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姑娘,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小说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给你可以进行替换的超能力,你将怎么做?又或者因为你的超能力,你的周围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家通过两个现实空间意象来探讨这个足够吸引我们的问题。在细节描写中,“我”不断在自我认知的现实空间和他者确认的现实空间中进行切换,爱恨交加,痛苦与享受,麻木与自责反复袭扰着“我”。“我”本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如果没有变故,就这样普普通通生活着的邮递员。按说,除了卖汽水的老奶奶,人人都喜欢“我”,“我”也“喜欢那时的我”,即便存在“日复一日的疲惫让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但当“我的自行车从土坡上飞速地滑下去,那让我体验到一种没有了任何羁绊的自由”。为了这份“和平淡的日子交换一些值得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我”宁愿冒“可能撞得头破血流的危险”。当第一节正常叙述的一场车祸不可思议地凭空消失的时候,“我”就同时踏入了他人印证的和自我认定的两个现实中。到底哪个现实是现实?“我”意识中的现实还是别人眼中的现实?“我”找不到答案,二者剧烈地冲突,使“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这件事情,“只能依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困扰与纠结让“我”想到了自杀,也许这是解脱的方式,可是要解脱什么呢?在派出所的经历似乎是一种正叙的现实故事,“我”也似乎保持着正常人的情感、逻辑,即使“我”为此而感到痛苦。爱情的降临使他者和自我两个现实合并成一个现实。与H小姐相爱以后,“我”不再是浑浑噩噩的局外人。“我”一度享受“替换”的超能力带来的美好,当然更渴望爱的真实,以至于宁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去极力保护那份真实的“爱”。无法调和的矛盾,在随后被H小姐支配的一轮又一轮“替换”他人的过程中集中到爆发的顶点。成为H小姐的工具人,并不是H小姐有什么能力控制“我”,而是爱让“我”迷失,“第三轮的‘替换’完全就是毫无人性的清洗”。杀掉H小姐,意味着所有的罪过都是H小姐,“我”还是那个善良的人,但当“我”终于替换掉自己,得以从事实犯罪中脱逃,并与狱方签订协议掩盖真相的时候,“我”从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执拗地想探求真相的人变成了对于真相“并不重要”的人,而“要紧的是把我放出来了,……”。小说结尾“我坐在监狱提供的面包车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到处都是女人,我不由得哭了出来”。“我”的哭是在庆幸还是在自责, “我”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始作俑者,一个即便有了超能力也难脱俗套的自私的人。生活现实孕育的道理往往隐藏在充满情感活力的意象背后,当凌乱琐屑的现实生活片段被设计为意象而被小说的生活世界所统摄,作家的表达即成为创作的动力,作品则基于表达的需要而呈现出写实与写意交融的艺术表现力。

内蒙古青年作家们
《一朵芍药一片海》中诺敏生活的草原有一朵芍药,而在她的心里驻留着一片来草原画画儿的、来自海边的男人给他描摹的大海。这个男人无情地离开了,他们一次邂逅的孩子出生即夭折,葬在了他们邂逅的芍药花丛里。诺敏总是愿意站在山顶,遥望整片天空、草原和山脉,然后张开双臂准备飞翔,心里想着“有一双翅膀就好了”。“她每次都会展开双臂,摆出一副飞翔的样子。”父亲阿古拉将从额麻麻家抢来的牧场命名诺敏牧场,“至少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它叫诺敏牧场,是我姑娘的土地”。额麻麻家的孙子苏亚拉深爱着诺敏,可每当苏亚拉靠近诺敏的时候,总是被诺敏呵斥“滚出我的牧场”。苏亚拉“昨天、前天、大前天,他都在望远镜里看见诺敏跳下马背,蹲在一丛芍药花旁边”。“她不理会被吹乱的头发却总是去擦拭被风吹出来的泪水。”“苏亚拉恨那个男人,他真后悔当初没有打断他的腿,后悔没有扎破他的车胎。”诺敏对闯入家中的小黑蛇动作利落地斩为几截,对闯入心里的爱情却无能为力。娜仁对蛇心怀恐惧,可她的生活里却总是被蛇闯入,她曾经被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冒白气的洞穴吸引,前去看到了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白的、黑的……一窝蛇。她怀上诺敏时梦见一条通体雪白的小白蛇,从空中飘下来,钻进了她的裤管里。诺敏跟海边来的男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飞刀斩杀眼看就要钻进画架旁边芍药丛里一条草绿色的蛇,母亲娜仁“中午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浑身无力,晕过去了”。“……突然晕过去不说脸还变绿了,就跟草一个颜色。”诺敏不由得想起了那条被她砍成两截的草绿色的蛇。诺敏想要试图出走,而每次她向父母提出这样的想法时,母亲娜仁就会恰逢其时地晕倒,娜仁希望诺敏留在自己身边,即使用晕倒的办法也要留住女儿,一想到女儿可能会受到伤害,她就喘不过气来,她又梦见了蛇:“我梦见了彩色的风、雪白的蛇,她们从我身体里钻出来,一滴眼泪载着它们飘走了。”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与亲情纠葛的故事。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闯入者,说不清谁闯入了谁的世界,就像娜仁埋葬分成几截的小黑蛇时想的“这条蛇不是第一个闯入者,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闯入者”。她和阿古拉说起那一窝蛇的时候想的“还不知道谁是闯入者呢,就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就好”。这又是一个似乎命运安排的闯入者的故事,闯入者带来的是对原有秩序的冲击,现实的、理想的,爱情的、亲情的,“井水不犯河水”不过是一厢情愿,随着开发旅游区的外来者将她孩子的尸骨挖出来,诺敏的伤痛达到极致,一群毫不相干的闯入者终结了所有人现实与情感中的既有安排。芍药、大海、蛇以显在的客观意象与亲情、爱情交融在一起,借诺敏之口表达出无限的感慨和思索,“她和他之间,她和孩子之间,她和阿爸阿妈之间,她和苏亚拉之间,她和外界之间,她和大自然之间间隔的是什么呢”。
《醉驼》围绕着家里的公驼依热毕思发情前后人们关注点的不同展开故事,父亲达楞泰想尽一切办法促其发情并生下很多的小白驼,壮大自己的驼群。小女儿米都格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一心想着离开故乡,离开草原。大女儿萨格萨原本和妹妹一样向往草原之外的世界,但是由于母亲的病逝,自己主动承担起照顾家人为父亲分担的女主人的角色。女婿英嘎在一场酒驾的事故中摔坏了脑袋,变得憨傻。达楞泰的父亲九斤为了治好孙女婿的病每天不厌其烦地弹唱江格尔,希望江格尔的故事可以治好英嘎憨傻的病,并在家庭出现的任何变故中化解每个人躁动不安的情绪。最终还是没有任何追求和想法的英嘎在江格尔故事激发出的勇敢中战胜了发情后性情大变的公驼,随着依热毕思的倒下,英嘎的憨傻病居然也好了。而有追求有想法的父亲、姐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有挣脱困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达楞泰一直思考女婿的病为什么突然好了,九斤老人告诉他“你去野地走走,多走走,自然就明白了”。醉驼的故事就是草原生活的现实,但英嘎的突然恢复则是一个传奇的书写,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写实无论着墨多少,都因这个传奇的书写而将读者引入“言不尽意”的审美意象中。或许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所期待的现实生活走向总是为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但生活同自然一样遵循自然的规律,沿着规律的方向耐心等待,生活赏赐我们的可能是更加美好的果实。当然,写意的表达由于其内在演化的特征,还可能有更多的指向。

《小说面面观》 (英)福斯特 著
《美好的一天》构建了一个美好的故事来叙说“生命和死亡”的主题。格乐巴和巴尔斯夫是两个在哈鲁娜怜悯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反复讨论这位善良且坚毅的女性是否在今天真正地离他们而去,标本鸟的“复活”让他们意识到哈鲁娜是真正地死亡了,他们称这一天为“美好的一天”,因为哈鲁娜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带着标本鸟的身体飞向自由。而她给予他们的怜爱永远深藏于心中,得到了灵魂的永生。标本鸟的“复活”、巴尔斯夫坐在尸体旁边咀嚼虫子、保姆对于哈鲁娜死亡的乐观等,都以表现手法的荒诞离奇映衬着身体这副皮囊的不堪与灵魂的真正永生。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孩童般的表达方式将“生命和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而充满意味。《扎穆沁》中的“我”曾经是一名高学历的人才,但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夏天,“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走上了二十年来一程又一程的流浪之路,“我”无法面对道尔吉的死亡,所以“我”决定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放逐自己。作家没有给 “我”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我”只是一个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陷入心魔的行路人,小说的笔触一直在追随“我”内心的追寻,情绪描写和心灵告白为这个故事渲染了丰富的色彩和韵味。“我不停地走啊走,走了二十年。别人问我的名字,我会说,我叫扎穆沁。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一个流浪的人,一个漂泊的人。”结尾“我”的告白与小说题目“扎穆沁”蒙古语的意思“行路人”相得益彰,表现出作家在创作伊始就将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作为维系作品的主旨,在物与我、爱与美的协调之间,达成创作的目标。《逃跑的牙齿》从小孩子的视角展开,慈爱的祖父、可爱的小狗豆豆、充满灵气的羊“白云”等草原上的万事万物,无不蕴藉着生活的美好与和谐。与小伙伴陶笛的友谊更为自己的童年增添无限快乐,但从陶笛 “逃跑的牙齿”牵扯出的一系列故事,告诉我们这并非一部儿童成长小说,巴图鲁大叔并不是那个远近闻名的喜欢狼、保护狼的爱心大使,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且残忍的猎杀者。童年的世界陷落在成人贪得无厌的现实世界,如果叙事至此,便只是线索非常清晰的从儿童视角对人在现实利益面前两面性的批判,但28颗狼牙的故事,又把这一切拽回到“童话”世界里,作家想表达的东西则值得读者细细品味。《求你们告诉我》将读者卷入悬疑推理的叙事逻辑里,写实中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买卖同罪”的问题,但叙事的走向并非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事情的反转和赋予事情某一种理解却又无法解释,让我们不得不以为作家的注意力不在写实,而是自己胸臆的书写,小说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剪不断、理还乱”。小说结尾的开放式结局,则将作家的表达置换为读者的疑问,以答案的无数种可能引起读者的想象。《戛然而止》的故事性比较强,讲述了阿苗、阿兰、李清、陈子谅等一群拥有不同性格的年轻人的青春故事。作家对青春期孩子们的心理状态、行为描写观察得很仔细,刻画得很真实,在青春期无聊的冲动里,将那个年纪的勇敢和胆怯、无畏与无知、喜悦与悲伤一一呈现出来。小说以一场斗殴的严重后果“陈子谅瘫软地倒在了地上”收束,也以“诗意”的含蓄书写了作家对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表达:“他们的青春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了。那些疼痛的,深刻的,复杂的,所谓的人生在世苦海浮沉,漫过青春的堤坝,淹没了他们。” 阿苗、阿兰的性格刻画比较鲜明,但这不是小说创作的目的,她们的命运不是由性格决定的,小说只是通过她们作为青春期少女的经历,完成作家对青春期记忆的“感性的快感”的表达。《蓝胡子的邀请》采用第三人称“她”和“他”来讲述一个婚姻的故事,题目中的“蓝胡子”本身就充满意蕴,来自法国同名小说,后人用其指代花花公子或虐待老婆的男人。这就使小说想表达的思想非常清晰了。小说通过女人的视角呈现了婚姻中女性的困境,婚姻中的男人不一定是花花公子或者虐待女性的“蓝胡子”,但当一个男人走进婚姻,建立家庭,男人与异性朋友的所谓友谊是否产生边界感,将会决定婚姻中的女性是否陷入情感和精神恐慌的困境中。当她给她的编辑发去这样一条信息:“一个可能发生过的房间是不是远比已知发生过的房间更可怕?因为可能发生的那个房间发生的事情在人的心里永远没有结束。” 是否意味着她可能在这样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清冷之人》以一个人跳进钢水化作蒸汽为引子开篇,以“来吧,诗人”“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结尾。中间的叙事围绕一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爱情、没有工作的中年男人“他”展开,全文不做细节描写,而以抒情的笔调将一个男人现实的苦难经历掩饰在诗歌里,但“诗歌是深渊里向他伸出来的一双手” “……没有这双手他受不住”。无可选择的苦难与诗歌对苦难的消解建构起整篇小说的意境,“诗歌不会像生活那样放弃废物,它会让废物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让他醒过来……”小说没有过多的技巧和情节,而是以作家的真诚表达感动着读者。《雪原战争》讲述了北方雪原上一个叫努古斯的国家以及它的盟国如何顽强抵抗当时兵强马壮的扎拉尔至高主义联邦国防军从而保家卫国的故事,虚构的历史将神话、传奇与现实糅合进同一个时空,用努古斯国的“死局”与霍辰“牛车上的老人国”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发展问题,没有结局的希望与富饶中的灭亡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整篇故事异域情调浓厚,叙事方式、语言表达,以及读者在故事、现实、历史、神话中来回穿梭,在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中,被带入阿日斯兰描述“努古斯国死局”的意境中。

《哺乳期的女人 》 毕飞宇 著
这些作品的表达定位,使小说人物性格刻画离开了作品的重心,小说叙事以满足个人内化了的美感经验为目的进行建构,这种建构没有主观情绪的无序宣泄与呻吟,而是宁静的沉思,是作家关于人、人生、世界观察与体验的展示。毕飞宇在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指出:“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 [2]内蒙古青年作家的这些作品散发着鲜明的个性气质,他们将细致的写实与擅于呈现情感与精神世界的中国式写意相交融,实现作家重视作品精神和情感指向的艺术表达。同时他们深刻意识到中短篇小说的文体价值,在形式上探索表达世界的方式,虽然在写实与写意融合的意象表达方面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共同点,但每位作家在作品结构、语言、视角等方面,表达自己感受和认知的社会生活时均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再有,在叙事作品中,表达成为全篇的基调,容易降低故事本身对读者的吸引力,而悬念设置在叙事作品中可以有效刺激读者阅读时的心理反应。“一个故事自然是读者愿意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故事。如果一开头读者就猜出了一切,即使故事叙述得再好,我认为这故事也不成其为故事。”[3]如果故事不成其为故事,故事所承载的表达也就成了无本之末,他们恰当地运用了叙事中的悬念,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一句话:“……他会讲故事,他有使读者处于悬念之中并挑起读者的好奇心的质朴能力。”[4]与“五四”时期以来以表达感情为主的文学观念不同,他们是表达对人、人生、生活的认知、追索与悲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时代文学面貌的文本,在诸如语言风格、主题意蕴、审美意趣等方面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均值得更多视阈的关注和研究。
注 释:
[1] 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02页.
[2]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自序.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1页.
[3] 傅腾霄.小说技巧.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77页.
[4] 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第133页.
刊于《草原》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韩彦斌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长期带领研究生开展内蒙古文学创作情况调研和文学批评,指导学生完成的《新世纪内蒙古汉语创作散文研究》《新世纪内蒙古汉语创作散文的审美体验》《新时期四十年〈草原〉刊发散文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变迁》《“索龙嘎”奖获奖作品中汉语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叙事研究》等学位论文,较为系统地呈现出内蒙古文学创作在一定阶段或某些方面的创作实绩。
版权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机场南辅路5.5公里处
电话:0471-4934352传真:0471-4925404
投稿邮箱:nmgwlwycbzx@163.com